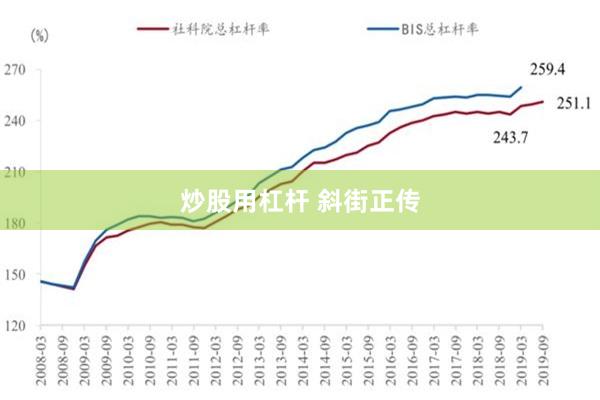
京城中轴线的“正楷”旁炒股用杠杆,偏安着一道历史的“行草”。
老北京城以中轴线对称布局,城内道路大多横平竖直,呈棋盘状分布。以“斜街”命名的胡同和小街巷却也并不鲜见,如大栅栏附近的杨梅竹斜街、什刹海旁的烟袋斜街。然而,以会馆林立、名人聚集、皇城文化与各省地方文化交流碰撞闻名的“斜街”,只有宣武门西南的上斜街。
这条约600米长的斜街,曾是古河道“银湾”的遗迹。元人的马蹄踏入河泥,明清赶考书生的麻履踩过霜痕,民国百姓的千层底碾过积雪。叠压的步履在古河床上层层锻打,终将时光夯成一条文明的甬道。
“小时候隐约听老家儿说起过,这里以前是一条河。”正在家门口下象棋的老街坊一边拱卒一边说,“‘出门奔斜街——不走正路’,说的就是它。”
上斜街的肌理中,藏着河流的旧影。元代兴建大都时,工匠们保留下了天然水系,得以让“银湾”的碧波穿城而过。至明清河道干涸,河床却未湮灭——南来北往的举子们在牛街北口折向东北,沿着故河道踩出一条“近路”。
史学家韩朴在《南城两翼斜街多》中还原了这幕奇景:从元大都到金中都来往最近的路,有一条是出南城北垣东端的崇智门,进大都南垣西端的顺承门,久而久之,在南城的废墟间形成了一条由西南向东北侧斜的捷径,这便是后来的下斜街与上斜街。
展开剩余72%到了明代,南方各省人员进京时,广安门是必经之路,而赶路的人为了近便,往往在牛街北口就向东北行进,顺着河流故道一路走向宣武门。长此以往,这些来来往往的人群就生生用脚在城南踩出了一条上斜街。真应了那句“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”。
上斜街的泥土里,曾渗着饱含法治思想的墨汁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刚搬进上斜街居所的沈家本在枕碧楼中伏案疾书,不远处护城河的涛声拍打着窗棂。这位花甲之年的法学家正面临毕生最艰难的抉择:是恪守《唐律疏议》的祖制,还是借鉴域外法理去疴革弊?凌迟枭首,非仁政也。他上书朝廷改革,斩断了延续千年的酷刑锁链。
2022年3月,这条因河而成的上斜街,入选《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(街巷胡同类 第一批)》。
春日午后,斜街路口。一路之隔的康乐里小学的同学们围拢在一起,听老师现场讲解斜街两旁历史上的会馆变迁。“上斜街两侧鼎盛时期的十二座会馆,曾是王朝鲜活的神经末梢……”
我一边旁听,一边脑补那些历史的片段:东莞新馆的门前,年羹尧旧部的铠甲声早已消散,取而代之的是粤籍商贾的南音;番禺会馆内龚自珍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墨迹尚未褪尽,曾随林则徐南下,为抗击英舰铸造过新式水雷的潘仕成又搬到此处。
最令人感动的是太原会馆屋檐下的雕花门——1923年秋,高君宇将一枚西山红叶夹在信中:“满山秋色关不住,一片红叶寄相思。”石评梅却在红叶背面题下“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”。两年后,才女在荒冢前,镌刻下“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,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”。
这些会馆的梁柱间,激荡着历史文化的风云。
沈家本总结扬弃古代法学思想,同时吸收西方现代法律理念,在枕碧楼修订《大清律例》,终成“中国近代法治的开拓者和引路人”。
大藏书家伦明迁居东莞新馆后,将自己在烂缦胡同东莞会馆的8间房全部用于藏书,并取名为“续书楼”,寄托了他决心续修《四库全书》的雄心壮志。续书楼中的藏书数万卷,由400多个藏书箱储存,其中绝大部分都是《四库全书》未曾收录的珍品。伦明最终将这数万卷藏书尽捐公库,践行了“化私为公”的箴言。
在前身是吴兴会馆的沈家本故居,讲解员介绍,这座见证中国法治近代化历程的院落自2018年开放以来,始终坚持免费开放。通过“枕碧会客厅”等品牌活动,将法治教育融入传统节日。2024年该故居因创新普法模式入选“西城家园优秀共建项目”,已经成为市民和游客了解法治文化的一扇窗口。
漫步上斜街,很难想象,曾经每年六月初六,这里竟会从书卷中苏醒,变成市井的戏台。
自明代起至清乾隆年间,宫廷中都有驯象的礼仪,上斜街附近设有一间驯象房。当时的大象多是东南亚各国进贡而来,待遇着实不错,有官阶、吃俸禄,还会参与皇家庆典——“洗象节”。
一位自称是雍正年间老账房后人的长者,至今记得祖上传下来的故事:“洗象日未至,酒肆二楼临窗位已预订一空。”民间流传,某年“洗象节”,一头公象突然扬起鼻子,将水柱喷向临街绣楼,惊得闺秀们钗环散落,反倒成就了几段“象为媒”的姻缘。顽童们躲在茶摊下突然跑出来拽象尾,差役举鞭笑骂:“小猢狲!这可是六品俸禄的‘仪卫’,比县太爷还尊贵!”
当暮色掠过伦明居所的瓦当炒股用杠杆,青石板上投下长长的影子。恍惚中,隐约可见当年的书生、法学家、革命者提着灯笼走过,他们的影子在斜街上拉得很长很长,一直延伸到历史的深处。 (杜文杰)
发布于:北京市